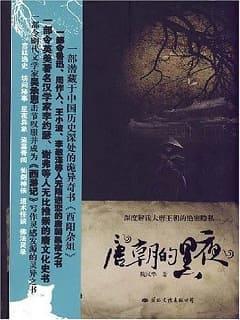杏书首页 我的书架 A-AA+ 去发书评 收藏 书签 手机
繁
第七章 盗侠:仙剑奇侠
2018-9-28 21:32
大盗鼻祖
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了一则关于中国大盗鼻祖盗跖的故事:
盗跖冢在河东,按盗跖死于东陵,此地古名东平陵,疑此近之。高堂县南有鲜卑城,旧传鲜卑聘燕,停于此矣。城傍有盗跖冢,冢极高大,贼盗尝私祈焉。齐天保初,土鼓县令丁永兴,有群贼劫其部内,兴乃密令人冢傍伺之,果有祈祀者,乃执诸县案杀之,自后祀者颇绝。
作为中国古代的大盗鼻祖,盗跖是春秋时人,带领兄弟横行为盗,在《庄子》中,专门有“盗跖篇”。在该篇中,盗跖把前来劝说他的孔子卷了个够。在此之前,孔子对盗跖的哥哥柳下季说:“你弟弟为害天下,你却不能教育他,那么让我来吧,我愿意替你去说说他。”
柳下季说:“大师,您就别操心了,去了也是白去。”
孔子不听,说:“放心吧,我很有经验的,肯定手到擒来,让他改邪归正。”
于是,孔子带着颜回、子贡两大弟子去见盗跖。帖子递上来,盗跖看完后说:“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?”随后一阵狂卷,把孔子骂得狗血喷头,最后阐明了“盗亦有道”的道理。该篇出现在《庄子》“杂篇”中,当为庄子的弟子所作,借盗跖之口,激烈地反对儒家思想。
按记载,盗跖墓在河东即现在的山西,而盗跖本人死于东陵即山东章丘。但在章丘附近的高堂县,也有一座盗跖墓,墓极高大,总有贼盗在出手前或得手后来这里拜祭他们祖师爷。北齐天保年间,旁边的土鼓县发生一起大案,县令丁永兴即埋伏人于盗跖墓边,果有群贼得手后前来祭祀,于是一网打尽。
倒霉就倒霉在偶像身上了。
顺便说一句,盗跖原名柳下跖,他的哥哥柳下季,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称呼:柳下惠。
事了拂衣去
刺客的历史非常悠久,在春秋和战国时代就非常活跃了。当时出现了职业刺客,为我们所熟悉的有聂政、专诸、豫让、要离、荆轲等。后来,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专门辟有“刺客列传”。汉魏六朝,刺客职业渐渐走入低谷,但到了唐朝,该职业再次勃兴起来。李白有名诗《侠客行》:“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!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”说的正是刺客。中唐以后,随着朝廷与藩镇的对立,刺客职业进入了高潮期。藩镇的节度使经常派刺客潜入首都刺杀宰相,其中以唐宪宗元和十年即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在长安大街上被刺案最为著名。《酉阳杂俎》中在“盗侠”门类中,多记载绿林剑侠的生活点滴,下面这则是涉及轻功的:
或言刺客,飞天夜叉术也。韩晋公在浙西,瓦官寺因商人无遮斋,众中有一年少请弄阁,乃投盖而上,单练镼履膜皮,猿挂鸟跂,捷若神鬼。复建罂水于结脊下,先溜至檐,空一足,欹身承其溜焉。睹者无不毛戴。
唐朝大臣、画家晋国公韩滉镇守浙西时,南京瓦官寺曾举行过一次无遮会。所谓无遮会,即是贵富贫贱无所区分的法会。这类法会往往由商人发起组织,在寺院里举行,其中穿插很多娱乐节目,但主要目的是商品交易,为现在庙会的前身。当时,在现场,有一少年表演轻功:飞檐走壁于楼阁间,一如猿鸟敏捷;又曾表演倒挂金钩的技巧,也称珍珠倒卷帘,两脚钩于高楼的檐瓦间,而身体悬空,随后快速地侧向移动,在场的人看后无不寒毛倒竖。
上面的少年应是杂技班子的成员。但按照史上记载,唐时很多刺客,即由杂技艺人转行而来。因此,很难说此少年日后不会成为一名刺客。该少年的轻功实在是太好了。说到轻功,它是刺客需要掌握的第一门要技。有人说刺客所掌握的轻功类似于飞天夜叉的本领,因为佛教中的飞天夜叉可在空中自由飞翔。对于一名优秀的刺客来说,可以没蛮力,但必须有轻功,蹿房跃脊,飞檐走壁,应如履平地一般,这即能保证你在短时间内接近行刺对象,也能保证你在行刺后迅速脱身。元和十年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案中,刺客就是隐藏在街道旁的大树上,在武元衡早朝途中,飘然而下,将其刺杀的。说到这里,必须提一下,树木是古代刺客隐身的首选,自武元衡被刺后,长安城内的政府要人皆将庭院内的大树砍掉,以防范被刺客利用。明清时代,北京故宫太和殿内无有一树,也是为了防止刺客。
暗器一种
段成式有个朋友叫广升,是长安慈恩寺僧人。据他回忆:在唐德宗贞元年间,四川阆州有一奇僧叫灵鉴,善以手指发射泥丸。当然不是普通的泥丸,这位和尚手中的泥丸是用以下配方制造的:洞庭湖岸边的沙土3斤、炭末儿3两、瓷器末儿1两、榆树皮半两、泔水2勺、紫矿(一种豆科植物)2两、细沙3分、藤纸(以古藤制成的纸张)5张,渴拓汁(不知什么玩意儿)半合,将这九种原料均匀搅拌,捣上至少三千杵,然后将其制成丸状,于阴处晾干,就成功了。随后的故事就跟这种暗器有关了,《酉阳杂俎》的记载是:
慈恩寺僧广升言,贞元末,阆州僧灵鉴善弹,其弹丸方: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,炭末三两,瓷末一两,榆皮半两,泔淀二勺,紫矿二两,细沙三分,藤纸五张,渴拓汁半合,九味和捣三千杵,齐手丸之,阴干。郑彙为刺史时,有当家名寅,读书,善饮酒,彙甚重之,后为盗,事发而死。寅尝诣灵鉴角放弹,寅指一枝节,其节目相去数十步,曰:“中之获五千。”一发而中,弹丸反射不破,至灵鉴乃陷节碎弹焉。
唐朝时有阆州刺史名叫郑彙,身边有个叫寅的门客,此人既好喝酒,又爱读书,还会舞枪弄棒,长于各种暗器,为郑彙器重。只是后来此人不学好,成了黑道中人,当了强盗,最终事发而死。在寅活着时,在郑彙的发起下,他与灵鉴和尚进行了一次弹丸较量。
那是唐朝的一个夏天吧,清风徐来,花叶不惊。在刺史的庭院里,朋友们闲坐着,侍女不时穿梭其间,突有人大叫:还不比呀?!于是,寅起身来到阶前,指着几十步外的一棵松树的某段枝节,对灵鉴说:“禅师!如果我击中了,当赢你五千钱,反之亦然!”
郑彙和他的朋友们表示赞同。寅说罢,从囊中取出一粒泥丸,用中指和食指相夹,甩出而击中,随后那泥丸又反弹了回来,没破碎。轮到灵鉴了,和尚起身,手指间夹着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泥丸,静默如偶,突然发力,宽袖飘荡,惊起树上的飞鸟。在众人诧异间,那泥丸已中目标,深深地碎陷于树中。
郑彙刺史带头鼓掌,大家齐声道:“神了。”
有人说,灵鉴手里的泥丸不是用九种材料制造的吗,怎么还碎了?看来这玩意儿不怎么样哦。不是那么回事。灵鉴的泥丸自然没问题,之所以碎于树中,只能说灵鉴发力更狠,内力更强。因为武林中人都知道,手发丸状暗器,最难的是既击中目标,又使其碎于目标中,要想达到这种境界需要特别的功力。而灵鉴可谓高手了,泥丸击中树后,既没弹回,也没在树外破碎,而是碎嵌于硬木中。如此推测,要是击中人的脑袋呢?由此看来,比之于灵鉴,寅手头上的功夫还嫩点,难怪后来没当好强盗。如果有灵鉴的功夫,逃跑时回头发射几粒,早就把官府的捕快们干掉了,也不致于最后被逮着处死。
寒林夜行
《酉阳杂俎》中“盗侠”门类中所记述的故事,成为后世武侠和仙剑小说的渊源。在烟树浩淼的唐朝之夜,在秋日的飒飒草莽中,发生了这样一件事:
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,暮止店中,更欲前进,店前老人方工作,曰:“客勿夜行,此中多盗。”韦曰:“某留心弧矢,无所患也。”因进发。行数十里,天黑,有人起草中尾之,韦叱不应,连发矢中之,复不退。矢尽,韦惧,奔马,有顷,风雨忽至,韦下马负一树,见空中有电光,相逐如鞠杖,势渐逼树杪,觉物纷纷坠其前。韦视之,乃木札也。须臾,积札埋至膝,韦惊惧,投弓矢,仰空乞命,拜数十,电光渐高而灭,风雷亦息,韦顾大树,枝干童矣,鞍驮已失,遂返前店。见老人方箍桶,韦意其异人,拜之,且谢有误也。老人笑曰:“客勿持弓矢,须知剑术。”引韦入院后,指鞍驮言:“却须取相试耳。”又出桶板一片,昨夜之箭悉中其上。韦请役力汲汤,不许,微露击剑事,韦亦得其一二焉。
中唐时期有人名叫韦行规,曾任兴州刺史。其人少年时,长于武艺,身手不凡,有大侠之风,而最擅长弓箭,百发百中,及至中年,他回忆起年少时的一段往事:当时他年轻气盛,爱慕侠义,旅行于山野间,拜访名师,寻访对手,一日游于长安西郊,天色已晚,暮色从远处的山峦中渐渐合围而来。当时大约是初秋吧,黄叶飘零,韦行规伫马于寒野中,顿生孤寂之感,又如进入了一幅秋夜的画卷。
在暮色隐约中,前方似有一小客栈,亮着昏黄的灯火。韦行规奔马止于店前。欲吃些东西。在凄白的月光下,他拖着长长的身影进入客栈。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后,他竟没有发现这里的主人,韦行规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正欲退出,只觉得身后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他猛然回头,却空无一人。再侧脸观看,只见马厩边靠着一位老者,正冲他诡异地微笑:“你要住店吗?”
韦行规说:“我只是路过而已,不想住下,现在即将前行。”不知为什么,他突然想尽快离开这里。
老者说:“我劝你还是不要夜行,长安西野,山高草深,此中多盗!”
韦行规此时已转身而行,并未回头:“我有弓箭在身,没什么可怕的,请您不要担心。”
老者不再说话,只是“呵呵”地笑了一声。
韦行规奔马而行,走了数十里,天已完全黑下来,此时两旁草莽渐深,前面的路似乎走不到尽头。除了枭鸣草动外,只有一片独属于荒野的寂静。韦行规骑马走着走着,感到有些不对,在冥冥中,觉得有人在身后的草莽中潜行,一直跟着他。想到这里,他的心忽地颤动了一下。
韦行规大声喊道:“何人?!”
后面没有动静。韦行规猛然回头,确见草莽中有人影晃动,他连发数箭,但其人如鬼魅一般依旧不退。此时韦行规囊中的箭已没了,他感到恐惧,纵马狂奔。没过多长时间,风起雨至。不知道往前跑了多远,雨幕愈密,韦行规下马后在一棵大树下避雨。此时,空中有电光闪烁,其势渐逼树顶,而风雷大作。韦行规再望,只觉得,在电光中,大树上有黑影如人,手中执长剑而舞。惊惧间,他感到有树枝木条纷纷而落,不一会儿,就已埋到自己的膝盖处了。韦行规大恐,扔掉手中的弓,仰空而拜。过了一会儿,电光渐渐高去而灭,风雷也停止。韦行规再看那大树,枝条尽落,像被长剑所削。而自己的马鞍也没了。
韦行规瘫倒在树下。
天快亮时,韦行规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那座小店,见老者正在院子里修理木桶,韦行规知其为异人,遂拜倒在地。老者笑道:“你不要只觉得会射弓箭就可以了,侠之大者,须知剑术。”韦行规急忙点头。随后,那老者引韦行规入后院,其马鞍正在地上。那老者又指地上的一片桶板,韦行规上前观看,昨夜他射出的那几枝箭,都插在上面。韦行规欲拜其为师,但被拒绝,老者只是给他讲了一下侠客与剑道的关系。由此透露出一个消息:从唐朝开始,“侠”与“剑”已难分形影了。
且说韦行规,拜师不得,出了小店,此时红日已从远山升起,走了一段路程,回望那京西小店,依旧掩映在秋日的寒林间……
七剑
下面的故事,仍是关于剑客的,文中主人公的剑术之精湛,随读而知之。在《酉阳杂俎》中是这样描述的:
黎干为京兆尹,时曲江涂龙祈雨,观者数千,黎至,独有老人植杖不避,干怒,杖背二十,如击鞔革,掉臂而去。黎疑其非常人,命老坊卒寻之,至兰陵里之内,入小门,大言曰:“我今日困辱甚,可具汤也。”坊卒遽返白黎,黎大惧,因弊衣怀公服,与坊卒至其处,时已昏黑,坊卒直入,通黎之官阀,黎唯趋而入,拜伏曰:“向迷丈人物色,罪当十死。”老人惊起,曰:“谁引君来此?”即牵上阶,黎知可以理夺,徐曰:“某为京兆尹,威稍损则失官政。丈人埋形杂迹,非证彗眼不能知也。若以此罪人,是钓人以贼,非义士之心也。”老人笑曰:“老夫之过。”乃具酒设席于地,招访卒令坐。夜深,语及养生之术,言约理辩,黎转敬惧,因曰:“老夫有一伎,请为尹设。”遂入,良久,紫衣朱,拥剑长短七口,舞于庭中,迭跃挥霍,换光电激,或横若裂盘,旋若规尺,有短剑二尺余,时时及黎之衽,黎叩头股栗。食顷,掷剑植地如北斗状,顾黎曰:“向试黎君胆气。”黎拜曰:“今日已后性命丈人所赐,乞役左右。”老人曰:“君骨相无道气,非可遽教,别日更相顾也。”揖黎而入。黎归,气色如病,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。翌日复往,室已空矣。
黎干为唐朝中期大臣,喜欢左道旁门之术,唐代宗时任京兆尹即长安市长,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:一年入夏,长安无雨,黎干组织人在曲江畔祈雨,观者有数千人。怎么那么多人呢?因为作为长安市长的黎干,将亲自扮演巫师,登台求雨。当黎市长的车队开到时,众人皆躲避,唯有一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那里。黎干大怒,叫人打了那老人二十棍子,那老人似乎没什么反应,转身而去。
后施刑者向黎干报告,棍子打在老人身上,就如同打在柔软的皮革上。黎干怀疑老人不同寻常,于是叫身边的老卒去查访。至长安兰陵里,左寻右觅,入一小门,听到那老人的声音:“我今日受辱,你们给我打点热水去。”
老卒回去后把事情告诉黎干,后者很害怕,穿了便衣与老卒赶至兰陵里,其时天色已昏,黎干入得院内,拜倒于老人面前。老人大惊:“谁把你引到这里的?”
黎干再拜,也为自己开脱了一下:“我为长安市长,若威仪尽失,也不是为官之道。您混迹于众人间,除非有慧眼而不能识。现在,我已知罪,您若不原谅我,也非拥有义士之心。”
老人笑道:“那是老夫之过了。”
黎干没答茬儿。老人也不再问,随后设酒席,一起喝起酒来。至夜深,老人纵论仙道侠义,黎干敬畏。老人说:“老夫有一技,请允许我为您表演。”遂入屋中,良久而出,已换上一身紫衣,双手竟拿着长短宝剑七把之多,舞于庭中,腾步飞跃,上下挥动,剑光一如星月闪烁,劈斩所至,自觉裂盘断石。只见那老人,飞速旋转,一如陀螺,只见剑光而不见其人。其间,有剑不时掠过黎干的面前,使后者战栗不已。最后,老人掷剑于空,落下后,七把剑插于地上,呈北斗七星之形。老人对黎干说:“我只是试试你的胆气,还不错。”
黎干又拜,说:“我命为您所赐,希望能拜您为师。”
老人说:“你骨相无道气,我不可收你为徒,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!”说罢,转身进了屋子。
黎干在惊悸中回到家,照镜子时,发现自己的胡须被老人剃掉了一寸多长。转天,黎干再去兰陵里寻找那位老人,但屋院内空无一人。
黎干是唐朝时担任首都长安市长时间最长的一个官员,先后八年。对于他,人们的评价是毁誉参半。此人仕途之路甚为奇怪,既非进士出身,也不是以顶级大族的后代接班,而是靠其所擅长的星算占卜之术,被聘为翰林学士,在唐代宗时颇为受宠,升任京兆尹,封寿春公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曲江求雨时,作为首都的最高行政长官,黎干自己登台扮演巫师的原因。当然,这也是导致他口碑不好的一个原因,史上的评价是:性情险涩,好旁门左道之妖术。但也有人说黎干不错,在长达八年的长安市长任期中,其人虽刻薄,但办事效率颇高,把长安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唐代宗在时,黎干与受宠的宦官刘忠翼交往密切,德宗即位后又多次化妆秘密与刘会晤,也不知道想要干什么,终被告发,被贬流放。黎前市长出发之日,“市里儿童数千人噪聚,怀瓦砾投击之,捕贼尉不能止。”也就是说,当日长安儿童好几千人冲着黎干扔石块。可见其人缘确实不佳。代宗时,黎干与刘忠翼曾欲改立太子,后德宗想起此事情,觉得流放黎干实在是便宜他,于是又追加了一道命令:赐死蓝田驿。我们不知道在被赐死时黎干是否会想起当年兰陵里的一幕:那位剑仙老人又去哪里了?能否会神奇地出现在他面前将他拯救?那老人终于没来,但他最后说的一句话,黎干还记得:“你骨相无道气,我不可收你为徒,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!”这“以后”竟是阴阳永绝,只有那七把宝剑在生命最后的光阴中惨淡地飞舞。其中一把,终于属于了他。这一次,不是割他的胡子,而是要他的命。
黎干生时不受长安市民待见,但他的一位部下没有忘记他,在路过长安开化里黎宅时,写有一首《至开化里寿春公故宅》:“宁知府中吏,故宅一徘徊。历阶存往敬,瞻位泣余哀。废井没荒草,阴牖生绿苔。门前车马散,非复昔时来……”这位部下是唐朝著名的山水诗人韦应物。
飞飞传
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的这则盗侠故事,被作家王小波改编为短篇小说《夜行记》:
建中初,士人韦生,移家汝州,中路逢一僧,因与连镳,有论颇洽,日将衔山,僧指路谓曰:“此数里是贫道兰若,郎君岂不能左顾乎?”士人许之,因令家口先行,僧即处分步者先排。比行十余里,不至,韦生问之,即指一处林烟曰:“此是矣。”又前进,日已没,韦生疑之,素善弹,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弹,怀铜丸十余,方责僧曰:“弟子有程期,适偶贪上人清论,勉副相邀。今已行二十里不至,何也?”僧但言且行,至是,僧前行百余步,韦知其盗也,乃弹之,僧正中其脑,僧初不觉,凡五发中之,僧始扪中处,徐曰:“郎君莫恶作剧。”韦知无奈何,亦不复弹。见僧方至一庄,数十人列炬出迎。僧延韦坐一厅中,唤云:“郎君勿忧。”因问左右:“夫人下处如法无?”复曰:“郎君且自慰安之,即就此也。”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,供帐甚盛,相顾涕泣。即就僧,僧前执韦生手曰:“贫道,盗也,本无好意,不知郎君艺若此,非贫道亦不支也,今日故无他,幸不疑也,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。”乃举手搦脑后,五丸坠地焉,盖脑衔弹丸而无伤。有顷布筵,具蒸犊,犊劄刀子十余,以齑饼环之。揖韦生就坐,复曰:“贫道有义弟数人,欲令伏谒。”言未已,朱衣巨带者五六辈,列于阶下。僧呼曰:“拜郎君,汝等向遇郎君,则成齑粉矣。”食毕,僧曰:“贫道久为此业,今向迟暮,欲改前非。不幸有一子,技过老僧,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。”乃呼飞飞出参郎君。飞飞年才十六七,碧衣长袖,皮肉如脂。僧叱曰:“向后堂侍郎君。”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,且曰:“乞郎君尽艺杀之,无为老僧累也。”引韦入一堂中,乃反锁之,堂中四隅,明灯而已。飞飞当堂执一短马鞭,韦引弹,意必中,丸已敲落。不觉跳在梁上,循壁虚摄,捷若猿攫,弹丸尽不复中。韦乃运剑逐之,飞飞倏忽逗闪,去韦身不尺。韦断其鞭节,竟不能伤。僧久乃开门,问韦:“与老僧除得害乎?”韦具言之,僧怅然,顾飞飞曰:“郎君证成汝为贼也,知复如何?”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,天将晓,僧送韦路口,赠绢百疋,垂泣而别。
唐德宗建中初年士人韦生搬家去汝州,行至荒野,路遇一僧,相谈甚欢。其时天色将晚,僧人指前路道:“再过几里,便是我的禅院,可否光顾?”
韦生答应,叫家眷先行,自己则相随那僧人。走了十多里地,依旧不至,韦生问僧人,后者指着前方的一处林烟,说:“那就是。”
又走了一段路,天已全黑,韦生开始怀疑僧人。韦生平素擅长弹弓奇技,百发百中,于是悄悄从靴中取出弹弓,装上铜弹丸,对那僧人说:“我赶路是有程期的,路上相遇,因相谈投机,所以共行,并接受您的邀请,可现在已走了二十多里,依旧不到,你是什么意思呢?”
僧人只说:“跟我走好了。”
僧人又往前走了百余步,韦生已知其为大盗,于是在身后发射弹丸,正中其后脑。僧人似乎没什么感觉,韦生又连续发射,五发弹丸皆中其脑,僧人这才摸其后脑,说:“你别再搞恶作剧了好不好?”
韦生无可奈何。此时,二人行至一庄,有数十人举火炬出迎。僧人拉韦生来到中厅,说:“公子莫怕。”随后,又问左右:“这位公子的家眷安排好了吗?”左右遂引韦生去看,见其妻女别在一室,被安排得很好。随即韦生回到中厅,僧人握其手说:“我确是大盗,与您共行,本来无甚好意,欲行加害,但公子身怀绝技,为贫僧敬佩。当然,也就是我,若逢他人,早被您击倒而丢命了。您的弹丸都在这里——”说罢,僧人摸了一下后脑,五颗弹丸皆坠地有声,而其脑竟无伤痕。
韦生连说惭愧,随后二人夜宴。僧人说:“我有几个义弟,愿意引见给你。”不一会儿,进来红衣大汉五六名,列于阶下。僧人说:“快来拜见公子,若是你们遇到他,脑袋早就成齑粉了。”
吃完饭后,僧人说:“我虽为僧人,但做大盗已很长时间了,现年岁已高,欲改前非,可不幸有一逆子,名叫飞飞,其本领已高过我,我令其退出江湖,但不奏效,今晚你能否帮我将其除掉,以绝后患?”
正说着,飞飞出来了:“知有高人前来,我欲与之比拼武艺。”飞飞年方十六七岁,身着碧衣长袖,肤色如脂,看似羸弱,而目光如鹰视狼顾。
僧人呵斥:“退下,后堂相待!”
飞飞走后,僧人取出一把长剑并将地上的五枚弹丸捡起交给韦生,说:“希望你使尽浑身武艺,为我斩杀飞飞!”
韦生见僧人杀意真挚,遂入后堂,此时飞飞手持一马鞭站于堂中,房屋四角点着四盏蜡烛。韦生入堂后,即引弓发弹,心想必能击中飞飞,结果是弹丸叮当落下,再看飞飞,竟已现身梁上,沿壁而行,轻功了得。韦生大惊,又发弹丸,皆不中,遂举剑逐之。飞飞腾挪闪转,离韦生只有一尺的距离,韦虽砍断了其马鞭,但终不能伤其人。
这时候,僧人将门打开,问韦生可否除掉飞飞,韦生摇头而出。僧人怅然若失,对歪着头的飞飞说:“你此生终为盗贼,有什么办法呢?”
故事到这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当夜僧人与韦生共论剑艺,但可以想象在二人中间,始终有飞飞的阴影在徘徊。显然这少年才是后来居上的高手。
上面的故事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影响很大。在明朝时,王世贞编辑了一本书叫《剑侠传》收入唐朝及以后的仙剑奇侠小说33篇,其中就包括段成式的这几篇作品。
炼银术之夜
《酉阳杂俎》所载的下面这个故事,不仅讲到神秘的炼银术,还涉及刺客和一段诡异的旅途:
元和中,江淮中唐山人者,涉猎史传,好道,常游名山,自言善缩锡,颇有师之者,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,气相合。卢亦语及炉火,称唐族乃外氏,遂呼唐为舅,唐不能相舍,因邀同之南岳。卢亦言亲故在阳羡,将访之,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。中途止一兰若,夜半语笑方酣,卢曰:“知舅善缩锡,可以梗概语之?”唐笑曰:“某数十年重趼从师,只得此术,岂可轻道耶?”卢复祈之不已,唐辞以师授有时,可达岳中相传。卢因作色:“舅今夕须传,勿等闲也。”唐责之:“某与公风马牛耳,不意盱眙相遇。实慕君子,何至驺卒不若也。”卢攘臂瞋目,眄之良久曰:“某刺客也。舅不得,将死于此。”因怀中探乌韦囊,出匕首,刃势如偃月,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扎。唐恐惧,具述。卢乃笑语唐:“几误杀舅。”此术十得五六,方谢曰:“某师,仙也,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。至添金缩锡,传者亦死。某久得乘跷之道者。”因拱揖唐,忽失所在。唐自后遇道流,辄陈此事戒之。
唐宪宗元和年间,江淮一带有一山人姓唐,好修道之术,遍游名山,自言会缩锡术。所谓缩锡术,即炼锡为银之术。可以想象,在当时有很多人想跟他学这一本领。不过,都被他拒绝了。
某日入暮,唐山人行至楚州客栈落脚,遇一青年自称卢生,说自己也颇懂些冶炼之术,二人聊得很投机。卢生自言母亲那边也姓唐,遂喊唐山人为舅舅,言辞恳切。唐山人说他自己此行去南岳衡山访友,问卢生可否同行,后者说自己去阳羡亲戚家,正好一道。
转天早上,二人踏上路途。天高水长,前路杳渺。行了一天,又至太阳落山,前面有一废弃的寺院,二人投宿其中,坐在草堆里,聊至半夜,才欲睡觉。这时候卢生突然说:“我知舅舅善于缩锡术,可将土锡锻化为白银,不知道能不能把技巧告诉我一些?”
唐山人笑道:“我数十年钻研此道,哪可轻传?我们还是睡觉吧。”
卢生乞求不已,唐山人无奈道:“此艺不是三语两言可讲得清楚的,若真想学,到衡山后可相传。”
卢生怒道:“舅舅!你今天晚上必须传授给我,其他莫废话!”
唐山人自然也恼了:“我与你风马牛不相及,只是路途偶遇,以为你是个君子,所以才搭伴同行,没想到你是如此粗野之人!”说罢,唐山人就想走。
卢生一把拉住唐山人,嘿嘿一笑:“你走得了么?”
唐山人有些惊恐,不知道此人到底想如何,又有什么目的。
卢生说:“实话告诉你吧,我是刺客。现在我依旧叫你舅舅,但如果舅舅不识相,就有可能死在这里。”说着,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,寒光闪烁,顺手拿起地上的一把铁熨斗,削之如木。
可怜的唐山人被吓坏了,只好把缩锡术一一道出。听后,卢生笑道:“刚才一时冲动,没把您吓坏了吧?”
唐山人又气又惧。卢生又说:“我师父乃得道之人,令我十弟子下山寻找天下妄传炼金术和炼银术的人,得而杀之。现在看来,你不是个轻传该术的人,我也就放心了。我现在即将离去,不能跟你同去衡山了,再见吧!”说完,他出门而去,消失在茫茫夜色中,只留下唐山人坐在草堆里发呆。
如上面所说,缩锡术即为炼银术,与炼金术同为古代道家方士修炼的内容之一。后人认为其术是荒唐的,但却不可否认它们是现代化学的渊源。在这个故事里,唐山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卢生盯上,至于后者的身份,他自称是得道者之徒,师父派他们十弟子下山追杀传授炼金术、炼银术之人。但是,在得到炼银术后,他就跑了。真相到底如何?在唐朝的那个晚上,这一切会聚成雾一般的谜团。
河西宋青春
古代志怪多涉及异剑奇器,在《酉阳杂俎》中也有所记载:
开元中,河西骑将宋青春,骁果暴戾,为众所忌。及西戎岁犯边,青春每阵常运臂大呼,执馘而旋,未尝中锋镝,西戎惮之,一军始赖焉。后吐蕃大地获生口数千,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:“尔何不能害青春?”答曰:“尝见青龙突阵而来,兵刃所及,若叩铜铁,我为神助将军也。”青春乃知剑之有灵。青春死后,剑为瓜州刺史李广琛所得,或风雨后,迸光出室,环烛方丈。哥舒镇西知之,求易以它宝,广琛不与,因赠诗:“刻舟寻化去,弹铗未酬恩。”
唐玄宗开元年间,河西边陲有骑将名叫宋青春,作战骁勇,性情暴戾,众人为惧。当时,西部边境战争不断,每与胡人厮杀时,宋青春往往振臂高呼,挥舞着自己的青龙长剑杀入阵中,最后割下敌人的耳朵凯旋而归,从未中过敌人的刀剑。
后来,吐蕃来犯,又被宋青春击败,唐军统帅叫翻译询问一个身着虎皮的吐蕃军校,为什么他们伤害不了宋青春?”
那军校回答:“每次宋将军临阵,我们在对面都会看到一条青龙随着他挥舞宝剑而飞动,我们的兵器与其宝剑一碰上,不是折断就是飞出手,我们认为青春将军有神助。”直到这时,宋青春才知道其手中的宝剑有灵。青春死后,剑为瓜州刺史李广琛所得,每遇风雨后,那剑兀自迸发光芒,照亮四周。大将哥舒翰镇守西部,得知此事,想用宝物与李广琛交换,但被拒绝,后者写诗相赠:“刻舟寻化去,弹铗未酬恩。”
关于异剑的故事,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还有一些:唐人郑云达,曾任大理寺卿,年轻时风神飒朗,颇有胆气,曾得一剑,甚为奇异,上有星光闪烁,舞动时有吼声。一晴日,郑云达坐于庭院,玩赏宝剑,忽有一人从庭树上飘然而下,着朱紫袍,虬发蓬松,提剑而立,身体四周有一圈黑气。郑知其非凡人,但假装没看到。那人直言:“我是天上之人,路过于此,知你最近得到一把异剑,想观看一下。”郑并不抬头,说:“什么异剑,只不过是一般的铁剑罢了,不值得您观看。你们上界之仙,还在乎这个吗?”那人依旧相求。郑不答语,伺机起身朝他刺去,没有击中,只有黑气一团落地,几天后才散去。
看来,奇异宝物,人皆爱之,仙亦不能免俗。
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了一则关于中国大盗鼻祖盗跖的故事:
盗跖冢在河东,按盗跖死于东陵,此地古名东平陵,疑此近之。高堂县南有鲜卑城,旧传鲜卑聘燕,停于此矣。城傍有盗跖冢,冢极高大,贼盗尝私祈焉。齐天保初,土鼓县令丁永兴,有群贼劫其部内,兴乃密令人冢傍伺之,果有祈祀者,乃执诸县案杀之,自后祀者颇绝。
作为中国古代的大盗鼻祖,盗跖是春秋时人,带领兄弟横行为盗,在《庄子》中,专门有“盗跖篇”。在该篇中,盗跖把前来劝说他的孔子卷了个够。在此之前,孔子对盗跖的哥哥柳下季说:“你弟弟为害天下,你却不能教育他,那么让我来吧,我愿意替你去说说他。”
柳下季说:“大师,您就别操心了,去了也是白去。”
孔子不听,说:“放心吧,我很有经验的,肯定手到擒来,让他改邪归正。”
于是,孔子带着颜回、子贡两大弟子去见盗跖。帖子递上来,盗跖看完后说:“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?”随后一阵狂卷,把孔子骂得狗血喷头,最后阐明了“盗亦有道”的道理。该篇出现在《庄子》“杂篇”中,当为庄子的弟子所作,借盗跖之口,激烈地反对儒家思想。
按记载,盗跖墓在河东即现在的山西,而盗跖本人死于东陵即山东章丘。但在章丘附近的高堂县,也有一座盗跖墓,墓极高大,总有贼盗在出手前或得手后来这里拜祭他们祖师爷。北齐天保年间,旁边的土鼓县发生一起大案,县令丁永兴即埋伏人于盗跖墓边,果有群贼得手后前来祭祀,于是一网打尽。
倒霉就倒霉在偶像身上了。
顺便说一句,盗跖原名柳下跖,他的哥哥柳下季,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称呼:柳下惠。
事了拂衣去
刺客的历史非常悠久,在春秋和战国时代就非常活跃了。当时出现了职业刺客,为我们所熟悉的有聂政、专诸、豫让、要离、荆轲等。后来,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专门辟有“刺客列传”。汉魏六朝,刺客职业渐渐走入低谷,但到了唐朝,该职业再次勃兴起来。李白有名诗《侠客行》:“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!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”说的正是刺客。中唐以后,随着朝廷与藩镇的对立,刺客职业进入了高潮期。藩镇的节度使经常派刺客潜入首都刺杀宰相,其中以唐宪宗元和十年即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在长安大街上被刺案最为著名。《酉阳杂俎》中在“盗侠”门类中,多记载绿林剑侠的生活点滴,下面这则是涉及轻功的:
或言刺客,飞天夜叉术也。韩晋公在浙西,瓦官寺因商人无遮斋,众中有一年少请弄阁,乃投盖而上,单练镼履膜皮,猿挂鸟跂,捷若神鬼。复建罂水于结脊下,先溜至檐,空一足,欹身承其溜焉。睹者无不毛戴。
唐朝大臣、画家晋国公韩滉镇守浙西时,南京瓦官寺曾举行过一次无遮会。所谓无遮会,即是贵富贫贱无所区分的法会。这类法会往往由商人发起组织,在寺院里举行,其中穿插很多娱乐节目,但主要目的是商品交易,为现在庙会的前身。当时,在现场,有一少年表演轻功:飞檐走壁于楼阁间,一如猿鸟敏捷;又曾表演倒挂金钩的技巧,也称珍珠倒卷帘,两脚钩于高楼的檐瓦间,而身体悬空,随后快速地侧向移动,在场的人看后无不寒毛倒竖。
上面的少年应是杂技班子的成员。但按照史上记载,唐时很多刺客,即由杂技艺人转行而来。因此,很难说此少年日后不会成为一名刺客。该少年的轻功实在是太好了。说到轻功,它是刺客需要掌握的第一门要技。有人说刺客所掌握的轻功类似于飞天夜叉的本领,因为佛教中的飞天夜叉可在空中自由飞翔。对于一名优秀的刺客来说,可以没蛮力,但必须有轻功,蹿房跃脊,飞檐走壁,应如履平地一般,这即能保证你在短时间内接近行刺对象,也能保证你在行刺后迅速脱身。元和十年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案中,刺客就是隐藏在街道旁的大树上,在武元衡早朝途中,飘然而下,将其刺杀的。说到这里,必须提一下,树木是古代刺客隐身的首选,自武元衡被刺后,长安城内的政府要人皆将庭院内的大树砍掉,以防范被刺客利用。明清时代,北京故宫太和殿内无有一树,也是为了防止刺客。
暗器一种
段成式有个朋友叫广升,是长安慈恩寺僧人。据他回忆:在唐德宗贞元年间,四川阆州有一奇僧叫灵鉴,善以手指发射泥丸。当然不是普通的泥丸,这位和尚手中的泥丸是用以下配方制造的:洞庭湖岸边的沙土3斤、炭末儿3两、瓷器末儿1两、榆树皮半两、泔水2勺、紫矿(一种豆科植物)2两、细沙3分、藤纸(以古藤制成的纸张)5张,渴拓汁(不知什么玩意儿)半合,将这九种原料均匀搅拌,捣上至少三千杵,然后将其制成丸状,于阴处晾干,就成功了。随后的故事就跟这种暗器有关了,《酉阳杂俎》的记载是:
慈恩寺僧广升言,贞元末,阆州僧灵鉴善弹,其弹丸方: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,炭末三两,瓷末一两,榆皮半两,泔淀二勺,紫矿二两,细沙三分,藤纸五张,渴拓汁半合,九味和捣三千杵,齐手丸之,阴干。郑彙为刺史时,有当家名寅,读书,善饮酒,彙甚重之,后为盗,事发而死。寅尝诣灵鉴角放弹,寅指一枝节,其节目相去数十步,曰:“中之获五千。”一发而中,弹丸反射不破,至灵鉴乃陷节碎弹焉。
唐朝时有阆州刺史名叫郑彙,身边有个叫寅的门客,此人既好喝酒,又爱读书,还会舞枪弄棒,长于各种暗器,为郑彙器重。只是后来此人不学好,成了黑道中人,当了强盗,最终事发而死。在寅活着时,在郑彙的发起下,他与灵鉴和尚进行了一次弹丸较量。
那是唐朝的一个夏天吧,清风徐来,花叶不惊。在刺史的庭院里,朋友们闲坐着,侍女不时穿梭其间,突有人大叫:还不比呀?!于是,寅起身来到阶前,指着几十步外的一棵松树的某段枝节,对灵鉴说:“禅师!如果我击中了,当赢你五千钱,反之亦然!”
郑彙和他的朋友们表示赞同。寅说罢,从囊中取出一粒泥丸,用中指和食指相夹,甩出而击中,随后那泥丸又反弹了回来,没破碎。轮到灵鉴了,和尚起身,手指间夹着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泥丸,静默如偶,突然发力,宽袖飘荡,惊起树上的飞鸟。在众人诧异间,那泥丸已中目标,深深地碎陷于树中。
郑彙刺史带头鼓掌,大家齐声道:“神了。”
有人说,灵鉴手里的泥丸不是用九种材料制造的吗,怎么还碎了?看来这玩意儿不怎么样哦。不是那么回事。灵鉴的泥丸自然没问题,之所以碎于树中,只能说灵鉴发力更狠,内力更强。因为武林中人都知道,手发丸状暗器,最难的是既击中目标,又使其碎于目标中,要想达到这种境界需要特别的功力。而灵鉴可谓高手了,泥丸击中树后,既没弹回,也没在树外破碎,而是碎嵌于硬木中。如此推测,要是击中人的脑袋呢?由此看来,比之于灵鉴,寅手头上的功夫还嫩点,难怪后来没当好强盗。如果有灵鉴的功夫,逃跑时回头发射几粒,早就把官府的捕快们干掉了,也不致于最后被逮着处死。
寒林夜行
《酉阳杂俎》中“盗侠”门类中所记述的故事,成为后世武侠和仙剑小说的渊源。在烟树浩淼的唐朝之夜,在秋日的飒飒草莽中,发生了这样一件事:
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,暮止店中,更欲前进,店前老人方工作,曰:“客勿夜行,此中多盗。”韦曰:“某留心弧矢,无所患也。”因进发。行数十里,天黑,有人起草中尾之,韦叱不应,连发矢中之,复不退。矢尽,韦惧,奔马,有顷,风雨忽至,韦下马负一树,见空中有电光,相逐如鞠杖,势渐逼树杪,觉物纷纷坠其前。韦视之,乃木札也。须臾,积札埋至膝,韦惊惧,投弓矢,仰空乞命,拜数十,电光渐高而灭,风雷亦息,韦顾大树,枝干童矣,鞍驮已失,遂返前店。见老人方箍桶,韦意其异人,拜之,且谢有误也。老人笑曰:“客勿持弓矢,须知剑术。”引韦入院后,指鞍驮言:“却须取相试耳。”又出桶板一片,昨夜之箭悉中其上。韦请役力汲汤,不许,微露击剑事,韦亦得其一二焉。
中唐时期有人名叫韦行规,曾任兴州刺史。其人少年时,长于武艺,身手不凡,有大侠之风,而最擅长弓箭,百发百中,及至中年,他回忆起年少时的一段往事:当时他年轻气盛,爱慕侠义,旅行于山野间,拜访名师,寻访对手,一日游于长安西郊,天色已晚,暮色从远处的山峦中渐渐合围而来。当时大约是初秋吧,黄叶飘零,韦行规伫马于寒野中,顿生孤寂之感,又如进入了一幅秋夜的画卷。
在暮色隐约中,前方似有一小客栈,亮着昏黄的灯火。韦行规奔马止于店前。欲吃些东西。在凄白的月光下,他拖着长长的身影进入客栈。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后,他竟没有发现这里的主人,韦行规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正欲退出,只觉得身后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他猛然回头,却空无一人。再侧脸观看,只见马厩边靠着一位老者,正冲他诡异地微笑:“你要住店吗?”
韦行规说:“我只是路过而已,不想住下,现在即将前行。”不知为什么,他突然想尽快离开这里。
老者说:“我劝你还是不要夜行,长安西野,山高草深,此中多盗!”
韦行规此时已转身而行,并未回头:“我有弓箭在身,没什么可怕的,请您不要担心。”
老者不再说话,只是“呵呵”地笑了一声。
韦行规奔马而行,走了数十里,天已完全黑下来,此时两旁草莽渐深,前面的路似乎走不到尽头。除了枭鸣草动外,只有一片独属于荒野的寂静。韦行规骑马走着走着,感到有些不对,在冥冥中,觉得有人在身后的草莽中潜行,一直跟着他。想到这里,他的心忽地颤动了一下。
韦行规大声喊道:“何人?!”
后面没有动静。韦行规猛然回头,确见草莽中有人影晃动,他连发数箭,但其人如鬼魅一般依旧不退。此时韦行规囊中的箭已没了,他感到恐惧,纵马狂奔。没过多长时间,风起雨至。不知道往前跑了多远,雨幕愈密,韦行规下马后在一棵大树下避雨。此时,空中有电光闪烁,其势渐逼树顶,而风雷大作。韦行规再望,只觉得,在电光中,大树上有黑影如人,手中执长剑而舞。惊惧间,他感到有树枝木条纷纷而落,不一会儿,就已埋到自己的膝盖处了。韦行规大恐,扔掉手中的弓,仰空而拜。过了一会儿,电光渐渐高去而灭,风雷也停止。韦行规再看那大树,枝条尽落,像被长剑所削。而自己的马鞍也没了。
韦行规瘫倒在树下。
天快亮时,韦行规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那座小店,见老者正在院子里修理木桶,韦行规知其为异人,遂拜倒在地。老者笑道:“你不要只觉得会射弓箭就可以了,侠之大者,须知剑术。”韦行规急忙点头。随后,那老者引韦行规入后院,其马鞍正在地上。那老者又指地上的一片桶板,韦行规上前观看,昨夜他射出的那几枝箭,都插在上面。韦行规欲拜其为师,但被拒绝,老者只是给他讲了一下侠客与剑道的关系。由此透露出一个消息:从唐朝开始,“侠”与“剑”已难分形影了。
且说韦行规,拜师不得,出了小店,此时红日已从远山升起,走了一段路程,回望那京西小店,依旧掩映在秋日的寒林间……
七剑
下面的故事,仍是关于剑客的,文中主人公的剑术之精湛,随读而知之。在《酉阳杂俎》中是这样描述的:
黎干为京兆尹,时曲江涂龙祈雨,观者数千,黎至,独有老人植杖不避,干怒,杖背二十,如击鞔革,掉臂而去。黎疑其非常人,命老坊卒寻之,至兰陵里之内,入小门,大言曰:“我今日困辱甚,可具汤也。”坊卒遽返白黎,黎大惧,因弊衣怀公服,与坊卒至其处,时已昏黑,坊卒直入,通黎之官阀,黎唯趋而入,拜伏曰:“向迷丈人物色,罪当十死。”老人惊起,曰:“谁引君来此?”即牵上阶,黎知可以理夺,徐曰:“某为京兆尹,威稍损则失官政。丈人埋形杂迹,非证彗眼不能知也。若以此罪人,是钓人以贼,非义士之心也。”老人笑曰:“老夫之过。”乃具酒设席于地,招访卒令坐。夜深,语及养生之术,言约理辩,黎转敬惧,因曰:“老夫有一伎,请为尹设。”遂入,良久,紫衣朱,拥剑长短七口,舞于庭中,迭跃挥霍,换光电激,或横若裂盘,旋若规尺,有短剑二尺余,时时及黎之衽,黎叩头股栗。食顷,掷剑植地如北斗状,顾黎曰:“向试黎君胆气。”黎拜曰:“今日已后性命丈人所赐,乞役左右。”老人曰:“君骨相无道气,非可遽教,别日更相顾也。”揖黎而入。黎归,气色如病,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。翌日复往,室已空矣。
黎干为唐朝中期大臣,喜欢左道旁门之术,唐代宗时任京兆尹即长安市长,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:一年入夏,长安无雨,黎干组织人在曲江畔祈雨,观者有数千人。怎么那么多人呢?因为作为长安市长的黎干,将亲自扮演巫师,登台求雨。当黎市长的车队开到时,众人皆躲避,唯有一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那里。黎干大怒,叫人打了那老人二十棍子,那老人似乎没什么反应,转身而去。
后施刑者向黎干报告,棍子打在老人身上,就如同打在柔软的皮革上。黎干怀疑老人不同寻常,于是叫身边的老卒去查访。至长安兰陵里,左寻右觅,入一小门,听到那老人的声音:“我今日受辱,你们给我打点热水去。”
老卒回去后把事情告诉黎干,后者很害怕,穿了便衣与老卒赶至兰陵里,其时天色已昏,黎干入得院内,拜倒于老人面前。老人大惊:“谁把你引到这里的?”
黎干再拜,也为自己开脱了一下:“我为长安市长,若威仪尽失,也不是为官之道。您混迹于众人间,除非有慧眼而不能识。现在,我已知罪,您若不原谅我,也非拥有义士之心。”
老人笑道:“那是老夫之过了。”
黎干没答茬儿。老人也不再问,随后设酒席,一起喝起酒来。至夜深,老人纵论仙道侠义,黎干敬畏。老人说:“老夫有一技,请允许我为您表演。”遂入屋中,良久而出,已换上一身紫衣,双手竟拿着长短宝剑七把之多,舞于庭中,腾步飞跃,上下挥动,剑光一如星月闪烁,劈斩所至,自觉裂盘断石。只见那老人,飞速旋转,一如陀螺,只见剑光而不见其人。其间,有剑不时掠过黎干的面前,使后者战栗不已。最后,老人掷剑于空,落下后,七把剑插于地上,呈北斗七星之形。老人对黎干说:“我只是试试你的胆气,还不错。”
黎干又拜,说:“我命为您所赐,希望能拜您为师。”
老人说:“你骨相无道气,我不可收你为徒,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!”说罢,转身进了屋子。
黎干在惊悸中回到家,照镜子时,发现自己的胡须被老人剃掉了一寸多长。转天,黎干再去兰陵里寻找那位老人,但屋院内空无一人。
黎干是唐朝时担任首都长安市长时间最长的一个官员,先后八年。对于他,人们的评价是毁誉参半。此人仕途之路甚为奇怪,既非进士出身,也不是以顶级大族的后代接班,而是靠其所擅长的星算占卜之术,被聘为翰林学士,在唐代宗时颇为受宠,升任京兆尹,封寿春公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曲江求雨时,作为首都的最高行政长官,黎干自己登台扮演巫师的原因。当然,这也是导致他口碑不好的一个原因,史上的评价是:性情险涩,好旁门左道之妖术。但也有人说黎干不错,在长达八年的长安市长任期中,其人虽刻薄,但办事效率颇高,把长安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唐代宗在时,黎干与受宠的宦官刘忠翼交往密切,德宗即位后又多次化妆秘密与刘会晤,也不知道想要干什么,终被告发,被贬流放。黎前市长出发之日,“市里儿童数千人噪聚,怀瓦砾投击之,捕贼尉不能止。”也就是说,当日长安儿童好几千人冲着黎干扔石块。可见其人缘确实不佳。代宗时,黎干与刘忠翼曾欲改立太子,后德宗想起此事情,觉得流放黎干实在是便宜他,于是又追加了一道命令:赐死蓝田驿。我们不知道在被赐死时黎干是否会想起当年兰陵里的一幕:那位剑仙老人又去哪里了?能否会神奇地出现在他面前将他拯救?那老人终于没来,但他最后说的一句话,黎干还记得:“你骨相无道气,我不可收你为徒,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!”这“以后”竟是阴阳永绝,只有那七把宝剑在生命最后的光阴中惨淡地飞舞。其中一把,终于属于了他。这一次,不是割他的胡子,而是要他的命。
黎干生时不受长安市民待见,但他的一位部下没有忘记他,在路过长安开化里黎宅时,写有一首《至开化里寿春公故宅》:“宁知府中吏,故宅一徘徊。历阶存往敬,瞻位泣余哀。废井没荒草,阴牖生绿苔。门前车马散,非复昔时来……”这位部下是唐朝著名的山水诗人韦应物。
飞飞传
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的这则盗侠故事,被作家王小波改编为短篇小说《夜行记》:
建中初,士人韦生,移家汝州,中路逢一僧,因与连镳,有论颇洽,日将衔山,僧指路谓曰:“此数里是贫道兰若,郎君岂不能左顾乎?”士人许之,因令家口先行,僧即处分步者先排。比行十余里,不至,韦生问之,即指一处林烟曰:“此是矣。”又前进,日已没,韦生疑之,素善弹,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弹,怀铜丸十余,方责僧曰:“弟子有程期,适偶贪上人清论,勉副相邀。今已行二十里不至,何也?”僧但言且行,至是,僧前行百余步,韦知其盗也,乃弹之,僧正中其脑,僧初不觉,凡五发中之,僧始扪中处,徐曰:“郎君莫恶作剧。”韦知无奈何,亦不复弹。见僧方至一庄,数十人列炬出迎。僧延韦坐一厅中,唤云:“郎君勿忧。”因问左右:“夫人下处如法无?”复曰:“郎君且自慰安之,即就此也。”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,供帐甚盛,相顾涕泣。即就僧,僧前执韦生手曰:“贫道,盗也,本无好意,不知郎君艺若此,非贫道亦不支也,今日故无他,幸不疑也,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。”乃举手搦脑后,五丸坠地焉,盖脑衔弹丸而无伤。有顷布筵,具蒸犊,犊劄刀子十余,以齑饼环之。揖韦生就坐,复曰:“贫道有义弟数人,欲令伏谒。”言未已,朱衣巨带者五六辈,列于阶下。僧呼曰:“拜郎君,汝等向遇郎君,则成齑粉矣。”食毕,僧曰:“贫道久为此业,今向迟暮,欲改前非。不幸有一子,技过老僧,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。”乃呼飞飞出参郎君。飞飞年才十六七,碧衣长袖,皮肉如脂。僧叱曰:“向后堂侍郎君。”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,且曰:“乞郎君尽艺杀之,无为老僧累也。”引韦入一堂中,乃反锁之,堂中四隅,明灯而已。飞飞当堂执一短马鞭,韦引弹,意必中,丸已敲落。不觉跳在梁上,循壁虚摄,捷若猿攫,弹丸尽不复中。韦乃运剑逐之,飞飞倏忽逗闪,去韦身不尺。韦断其鞭节,竟不能伤。僧久乃开门,问韦:“与老僧除得害乎?”韦具言之,僧怅然,顾飞飞曰:“郎君证成汝为贼也,知复如何?”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,天将晓,僧送韦路口,赠绢百疋,垂泣而别。
唐德宗建中初年士人韦生搬家去汝州,行至荒野,路遇一僧,相谈甚欢。其时天色将晚,僧人指前路道:“再过几里,便是我的禅院,可否光顾?”
韦生答应,叫家眷先行,自己则相随那僧人。走了十多里地,依旧不至,韦生问僧人,后者指着前方的一处林烟,说:“那就是。”
又走了一段路,天已全黑,韦生开始怀疑僧人。韦生平素擅长弹弓奇技,百发百中,于是悄悄从靴中取出弹弓,装上铜弹丸,对那僧人说:“我赶路是有程期的,路上相遇,因相谈投机,所以共行,并接受您的邀请,可现在已走了二十多里,依旧不到,你是什么意思呢?”
僧人只说:“跟我走好了。”
僧人又往前走了百余步,韦生已知其为大盗,于是在身后发射弹丸,正中其后脑。僧人似乎没什么感觉,韦生又连续发射,五发弹丸皆中其脑,僧人这才摸其后脑,说:“你别再搞恶作剧了好不好?”
韦生无可奈何。此时,二人行至一庄,有数十人举火炬出迎。僧人拉韦生来到中厅,说:“公子莫怕。”随后,又问左右:“这位公子的家眷安排好了吗?”左右遂引韦生去看,见其妻女别在一室,被安排得很好。随即韦生回到中厅,僧人握其手说:“我确是大盗,与您共行,本来无甚好意,欲行加害,但公子身怀绝技,为贫僧敬佩。当然,也就是我,若逢他人,早被您击倒而丢命了。您的弹丸都在这里——”说罢,僧人摸了一下后脑,五颗弹丸皆坠地有声,而其脑竟无伤痕。
韦生连说惭愧,随后二人夜宴。僧人说:“我有几个义弟,愿意引见给你。”不一会儿,进来红衣大汉五六名,列于阶下。僧人说:“快来拜见公子,若是你们遇到他,脑袋早就成齑粉了。”
吃完饭后,僧人说:“我虽为僧人,但做大盗已很长时间了,现年岁已高,欲改前非,可不幸有一逆子,名叫飞飞,其本领已高过我,我令其退出江湖,但不奏效,今晚你能否帮我将其除掉,以绝后患?”
正说着,飞飞出来了:“知有高人前来,我欲与之比拼武艺。”飞飞年方十六七岁,身着碧衣长袖,肤色如脂,看似羸弱,而目光如鹰视狼顾。
僧人呵斥:“退下,后堂相待!”
飞飞走后,僧人取出一把长剑并将地上的五枚弹丸捡起交给韦生,说:“希望你使尽浑身武艺,为我斩杀飞飞!”
韦生见僧人杀意真挚,遂入后堂,此时飞飞手持一马鞭站于堂中,房屋四角点着四盏蜡烛。韦生入堂后,即引弓发弹,心想必能击中飞飞,结果是弹丸叮当落下,再看飞飞,竟已现身梁上,沿壁而行,轻功了得。韦生大惊,又发弹丸,皆不中,遂举剑逐之。飞飞腾挪闪转,离韦生只有一尺的距离,韦虽砍断了其马鞭,但终不能伤其人。
这时候,僧人将门打开,问韦生可否除掉飞飞,韦生摇头而出。僧人怅然若失,对歪着头的飞飞说:“你此生终为盗贼,有什么办法呢?”
故事到这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当夜僧人与韦生共论剑艺,但可以想象在二人中间,始终有飞飞的阴影在徘徊。显然这少年才是后来居上的高手。
上面的故事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影响很大。在明朝时,王世贞编辑了一本书叫《剑侠传》收入唐朝及以后的仙剑奇侠小说33篇,其中就包括段成式的这几篇作品。
炼银术之夜
《酉阳杂俎》所载的下面这个故事,不仅讲到神秘的炼银术,还涉及刺客和一段诡异的旅途:
元和中,江淮中唐山人者,涉猎史传,好道,常游名山,自言善缩锡,颇有师之者,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,气相合。卢亦语及炉火,称唐族乃外氏,遂呼唐为舅,唐不能相舍,因邀同之南岳。卢亦言亲故在阳羡,将访之,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。中途止一兰若,夜半语笑方酣,卢曰:“知舅善缩锡,可以梗概语之?”唐笑曰:“某数十年重趼从师,只得此术,岂可轻道耶?”卢复祈之不已,唐辞以师授有时,可达岳中相传。卢因作色:“舅今夕须传,勿等闲也。”唐责之:“某与公风马牛耳,不意盱眙相遇。实慕君子,何至驺卒不若也。”卢攘臂瞋目,眄之良久曰:“某刺客也。舅不得,将死于此。”因怀中探乌韦囊,出匕首,刃势如偃月,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扎。唐恐惧,具述。卢乃笑语唐:“几误杀舅。”此术十得五六,方谢曰:“某师,仙也,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。至添金缩锡,传者亦死。某久得乘跷之道者。”因拱揖唐,忽失所在。唐自后遇道流,辄陈此事戒之。
唐宪宗元和年间,江淮一带有一山人姓唐,好修道之术,遍游名山,自言会缩锡术。所谓缩锡术,即炼锡为银之术。可以想象,在当时有很多人想跟他学这一本领。不过,都被他拒绝了。
某日入暮,唐山人行至楚州客栈落脚,遇一青年自称卢生,说自己也颇懂些冶炼之术,二人聊得很投机。卢生自言母亲那边也姓唐,遂喊唐山人为舅舅,言辞恳切。唐山人说他自己此行去南岳衡山访友,问卢生可否同行,后者说自己去阳羡亲戚家,正好一道。
转天早上,二人踏上路途。天高水长,前路杳渺。行了一天,又至太阳落山,前面有一废弃的寺院,二人投宿其中,坐在草堆里,聊至半夜,才欲睡觉。这时候卢生突然说:“我知舅舅善于缩锡术,可将土锡锻化为白银,不知道能不能把技巧告诉我一些?”
唐山人笑道:“我数十年钻研此道,哪可轻传?我们还是睡觉吧。”
卢生乞求不已,唐山人无奈道:“此艺不是三语两言可讲得清楚的,若真想学,到衡山后可相传。”
卢生怒道:“舅舅!你今天晚上必须传授给我,其他莫废话!”
唐山人自然也恼了:“我与你风马牛不相及,只是路途偶遇,以为你是个君子,所以才搭伴同行,没想到你是如此粗野之人!”说罢,唐山人就想走。
卢生一把拉住唐山人,嘿嘿一笑:“你走得了么?”
唐山人有些惊恐,不知道此人到底想如何,又有什么目的。
卢生说:“实话告诉你吧,我是刺客。现在我依旧叫你舅舅,但如果舅舅不识相,就有可能死在这里。”说着,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,寒光闪烁,顺手拿起地上的一把铁熨斗,削之如木。
可怜的唐山人被吓坏了,只好把缩锡术一一道出。听后,卢生笑道:“刚才一时冲动,没把您吓坏了吧?”
唐山人又气又惧。卢生又说:“我师父乃得道之人,令我十弟子下山寻找天下妄传炼金术和炼银术的人,得而杀之。现在看来,你不是个轻传该术的人,我也就放心了。我现在即将离去,不能跟你同去衡山了,再见吧!”说完,他出门而去,消失在茫茫夜色中,只留下唐山人坐在草堆里发呆。
如上面所说,缩锡术即为炼银术,与炼金术同为古代道家方士修炼的内容之一。后人认为其术是荒唐的,但却不可否认它们是现代化学的渊源。在这个故事里,唐山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卢生盯上,至于后者的身份,他自称是得道者之徒,师父派他们十弟子下山追杀传授炼金术、炼银术之人。但是,在得到炼银术后,他就跑了。真相到底如何?在唐朝的那个晚上,这一切会聚成雾一般的谜团。
河西宋青春
古代志怪多涉及异剑奇器,在《酉阳杂俎》中也有所记载:
开元中,河西骑将宋青春,骁果暴戾,为众所忌。及西戎岁犯边,青春每阵常运臂大呼,执馘而旋,未尝中锋镝,西戎惮之,一军始赖焉。后吐蕃大地获生口数千,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:“尔何不能害青春?”答曰:“尝见青龙突阵而来,兵刃所及,若叩铜铁,我为神助将军也。”青春乃知剑之有灵。青春死后,剑为瓜州刺史李广琛所得,或风雨后,迸光出室,环烛方丈。哥舒镇西知之,求易以它宝,广琛不与,因赠诗:“刻舟寻化去,弹铗未酬恩。”
唐玄宗开元年间,河西边陲有骑将名叫宋青春,作战骁勇,性情暴戾,众人为惧。当时,西部边境战争不断,每与胡人厮杀时,宋青春往往振臂高呼,挥舞着自己的青龙长剑杀入阵中,最后割下敌人的耳朵凯旋而归,从未中过敌人的刀剑。
后来,吐蕃来犯,又被宋青春击败,唐军统帅叫翻译询问一个身着虎皮的吐蕃军校,为什么他们伤害不了宋青春?”
那军校回答:“每次宋将军临阵,我们在对面都会看到一条青龙随着他挥舞宝剑而飞动,我们的兵器与其宝剑一碰上,不是折断就是飞出手,我们认为青春将军有神助。”直到这时,宋青春才知道其手中的宝剑有灵。青春死后,剑为瓜州刺史李广琛所得,每遇风雨后,那剑兀自迸发光芒,照亮四周。大将哥舒翰镇守西部,得知此事,想用宝物与李广琛交换,但被拒绝,后者写诗相赠:“刻舟寻化去,弹铗未酬恩。”
关于异剑的故事,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还有一些:唐人郑云达,曾任大理寺卿,年轻时风神飒朗,颇有胆气,曾得一剑,甚为奇异,上有星光闪烁,舞动时有吼声。一晴日,郑云达坐于庭院,玩赏宝剑,忽有一人从庭树上飘然而下,着朱紫袍,虬发蓬松,提剑而立,身体四周有一圈黑气。郑知其非凡人,但假装没看到。那人直言:“我是天上之人,路过于此,知你最近得到一把异剑,想观看一下。”郑并不抬头,说:“什么异剑,只不过是一般的铁剑罢了,不值得您观看。你们上界之仙,还在乎这个吗?”那人依旧相求。郑不答语,伺机起身朝他刺去,没有击中,只有黑气一团落地,几天后才散去。
看来,奇异宝物,人皆爱之,仙亦不能免俗。